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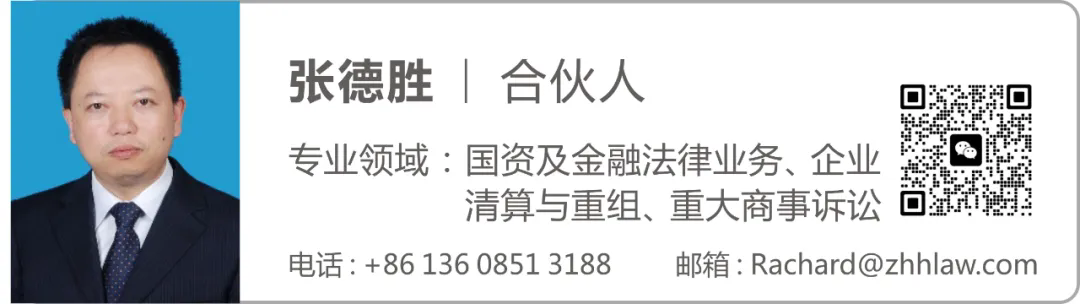
摘要:根據工商總局2014年發布的《全國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情況報告》,小微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堅實基礎”。小微企業的靈活性與多樣性增強了社會與經濟的彈性,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其設立、經營也必然伴隨著部分企業退出市場。世行在2023年宜商環境指數中也設計了“小微企業專門破產程序”指標,對我國營商環境建設帶來新的挑戰。我國現行的企業破產制度適用于所有大中小型企業,雖然我國部分法院對小微企業專門破產程序制定了相關工作指引等規定,但小微企業專門破產程序仍處于制度空白,亟待制定統一規則以完善,從而適應破產法現代化發展趨勢,促進市場良性發展。與此同時,我國對于小微企業的界定標準亦不統一,從工信部等相關國家職能部門劃型標準,到稅務部門核定劃型標準等,都各有不同。因此,破產法修改和建立小微企業專門破產制度的同時,應當需要對小微企業作出界定。本文梳理了各方對小微企業的劃型界定標準,擬對破產審理中的小微企業界定標準做一些思考和建議。
關鍵詞:小微企業 專門破產制度 營商環境 破產法修改
1 問題的由來
(一)世行對于小微企業破產的重視
2023年,世行發布了新營商環境評估的《方法論手冊》《說明及指南》,新體系B-READY的框架已初步搭建完成。在“商事破產指標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破產程序規制中,就在特別程序中將小微企業問題納入,包含了小微企業重整的可用性及標準、小微企業重整簡易程序向破產清算程序的轉換、針對小微企業的最低限度債務免除標準和不予免除條件。B-READY手冊認為,對小微企業來說,缺乏有吸引力的退出渠道可能會阻止許多企業家創業。到小微企業債務人啟動破產程序時,企業已經無法生存,這會導致價值損失,損害公司的完整性,損害法律程序的確定性。
(二)聯合國小微企業破產立法指南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小微企業破產法立法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指南》討論了簡易破產制度的特征,聚焦于更快捷、更簡單、便利易行和可負擔得起的破產程序,并同時附帶適當的保障措施。明確各國應當確保簡易破產制度適用于所有小微企業,制度涉及的方面可以根據小微企業的類型有所區別。《指南》旨在補充《貿易法委員會破產立法指南》,但對于小微企業均僅作類別區分的原則性描述,對于不同類型所對應的小微企業定義卻未予明確。
(三)我國對小微企業專門破產程序的需求
國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到中小微企業的“56789”,即中小微企業貢獻了50%的稅收、創造了60%以上的GDP、完成了70%的技術創新、提供了80%的城鎮勞動就業崗位、占企業總數的90%以上。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充分發揮司法職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業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有效發揮司法對中小微企業的拯救功能,引導企業通過破產重整、和解等程序,實現債務危機有效解決、債權人公平受償,使中小微企業獲得再生。各地也陸續出臺了一些關于辦理中小微企業破產案件指南或方案,以期尋求中小微企業破產的脫困之路。在近年破產法的修改中,也將小微企業的專門程序擬納入增加范圍。
2 我國非破產體系下界定小微企業的規定和標準
(一)中小企業促進法
2018年《中小企業促進法》(以下簡稱促進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中型、小型和微型企業劃分標準由國務院負責中小企業促進工作綜合管理的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報國務院批準。但該法實施后,中小企業促進辦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準的劃定指標并未及時更新。現行有效且實踐中使用得最多的,是2011年版工信部的劃型標準。
(二)工信部關于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及財政部于2011年6月18日發布了《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將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形,具體標準根據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筆者梳理劃型標準主要分為四大類:以營業收入、以營業收入加上從業人員數量、以營業收入加上資產總資以及僅考慮從業人員數量為指標。具體如下表:
|
劃型指標 |
行業類別 |
中小微范疇 |
中型標準 |
小型標準 |
微型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稅務關于小微企業劃型標準規定
1.企業所得稅減免所得稅額優惠中的“小微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28條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但對于小型微利企業的界定并未明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92條規定,企業所得稅法第28條第一款所稱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是指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元;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實施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22年第13號)中,稅務機關在認定小微企業時,需滿足三個條件: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3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5000萬元。
2.其他稅種劃型中的“小微企業”
財政部、稅務總局在增值稅留抵稅額政策中,對小微企業認定,通常情況按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和《金融業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中的納稅人考核認定,主要以資產總額和營業收入為主;而特別規定中,對于小微企業的劃型則以增值稅年銷售額為主。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關于延續實施制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繳部分稅費時,對于制造業的“小微企業”判定標準以企業年銷售額為主。財政部、稅務總局在實施小微企業“六稅兩費”減免時的認定標準,則以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結果為主。
綜上,稅務部門對于“小微企業”的界定標準更不統一。主要是按不同的稅種,以年度應納稅所得額、銷售額、從業人數、資產總額等方面進行考核劃型。
3 其他國家對于小微企業的界定
小微企業,甚至放寬至中小微企業,全球范圍內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定義。在不同法域,界定這類企業的因素包括年度總收入或凈收入、資產和/或負債、銷售額、法律結構,以及員工人數。①
員工10人以下,以及營業額≤200萬歐元或資產負債表≤200萬歐元的企業,為微型企業。員工在10以上50人以下的,以及營業額≤1000萬歐元或資產負債表≤1000萬歐元的企業,為小型企業。員工不足250人,以及營業額≤5000萬歐元或資產負債表≤4300萬歐元的企業,為中型企業。②
(二)美國只劃分小型企業,且具體債務門檻3年一調
美國對于中小微企業的劃分則更為特別。對于中型和微型企業無定義,而對于小型企業的定義為:從事商事或商業活動(主要經營不動產的除外),非或有無擔保債務及擔保債務總額不超過2566050美元。
破產法規定的具體債務門檻每3年會調整一次。但實際上,美國中小企業占所有企業的99%,雇用了超過50%的私營部門員工,并創造了私營部門凈新增就業崗位的65%。③
(三)日本劃型針對不同行業以資本金和員工數為標準
《日本中小企業基本法》第二條明確了中小企業者的范圍與用語的定義:根據本法作為政策實施對象的中小企業者,如以下各項所載。其范圍的確定是為了有效實現本法的目標和基本理念。
以制造業、建筑業、運輸業或其他行業(以下列舉除外)為主營業務,其資本金或出資總額在3億日元以下以及固定員工人數在300人以下的公司和個人;以批發業為主營業務,其資本金或出資總額在1億日元以下以及固定員工人數在100人以下的公司和個人;以服務業為主營業務,其資本金或出資總額在5000萬日元以下以及固定員工人數在100人以下的公司和個人;以零售業為主營業務,其資本金或出資總額在5000萬日元以下以及固定員工人數在50人以下的公司和個人。
該條第四款明確本法中的“小規模企業者”是指,固定員工大致在20人(如以商業或服務業為主營業務,則為5人)以下的從業者。④
4 目前國內小微企業破產的界定實踐
(一)《北京破產法庭中小微企業快速重整工作辦法(試行)》
北京一中院于2022年4月25日出臺全國首個專門規范中小微企業快速重整的制度規范《中小微企業快速重整工作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辦法規定,根據資產負債表、審計報告等財務資料,企業無財產擔保負債總額不超過1億元或符合國務院相關部門制定的中小微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中小微企業,債權債務關系明確,財產狀況清楚的,即滿足適用中小微企業快速重整的條件。同時,雖不符合上述標準,但經過庭外重組或者預重整程序,已經形成庭外重組方案或預重整方案的企業重整案件亦可參照適用辦法規定。
該指引更注重無財產擔保負債的總額,適用中小微企業快速重整的條件為債權債務關系明確,財產狀況清楚的情況下,可采用無財產擔保負債金額不超過一億元為標準,也可采用國務院相關部門關于中小微企業的劃型標準。但暫未涉及小微企業破產清算程序。
(二)南京中院出臺《關于推進小微企業破產保護的工作方案(試行)》
南京中院于2023年4月4日發布了《關于推進小微企業破產保護的工作方案(試行)》,建立了全國首個符合小微企業特點的破產清算、重整、和解全類型破產保護模式,適用于債權債務關系明確、財產狀況清楚、債務規模不大、債權人戶數不多的小微企業。
該工作方案更著重對于小微企業破產全流程的簡化,但對于適用的小微企業界定并未作明確的規定。
(三)上海破產法庭關于小微企業破產案件制定行動方案
上海破產法庭于2023年6月制定了關于依法高效辦理小微企業破產案件行動方案,方案對于小微企業的描述為“符合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的小微企業劃型標準”,對符合前述標準,且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債務人財產狀況清楚、負債規模較小的企業,可適用。
該方案對于小微企業的劃定還是沿用了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的劃型標準,同時需滿足相關條件,但對于條件中“負債規模較小”未作明確界定。
(四)重慶破產法庭發布《小微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指引(試行)》
重慶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8日發布《小微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指引(試行)》,旨在優化法治營商環境,助力小微企業良性發展。適用的小微企業破產案件的條件為需同時符合債務人主要財產權屬無爭議且易處置;債務人的債權債務關系相對明確;債權人人數在100人以下。
該指引更注重債權人人數規模,且對適用小微企業破產案件的條件為同時滿足,即需要符合物、關系、人三方面條件,但對于小微企業的實質認定標準未予明確。
綜上,各地法院陸續針對小微企業破產案件的辦理制定發布了相應的方案和指引,在破產案件辦理中,針對小微企業建立了簡要立案渠道、優化了繁簡分流機制和表決機制,探索庭外多元債務化解機制等方式。確實可以降低破產成本、提高辦案效率,但對于“小微企業”的界定卻并不明晰。
5 關于破產審理小微企業的界定標準的思考
破產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具有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的價值功能。發揮好破產制度作用,對于構建現代化市場主體救治和退出機制,貫徹落實“六穩”“六保”工作要求,優化營商環境有著重要意義。小微企業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界定小微企業、區分小微企業、建立并適用小微企業破產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市場發展以及優化營商環境。
(一)破產程序小微企業界定的必要性
1.法律的適用主體問題
以筆者所在的重慶為例,重慶破產法庭發布的2023年破產審判白皮書中對于企業規模的分析:破產及強制清算企業注冊資本覆蓋0.92萬元至42億元區間。注冊資本100萬元、100萬元至500萬元、500萬元至2000萬元、2000萬元至1億元、超過1億元的企業占比分別是16.83%、20.99%、33.66%、22.18%、6.34%。企業性質,破產及強制清算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78.42%。即破產及強清企業注冊資本主要集中在1億元以內;破產及強清中民營企業占據了大多數,這都符合我們通常理解的“小微企業”。按照重慶破產法庭小微企業審理指引來看,需要符合物、關系、人三方面條件,未涉及注冊資本,亦未對小微企業的實質認定標準予以明確。
從實踐來看,大量的破產案件均集中在中小微企業。而各部門、各行業對于小微企業的界定標準不統一,各地法院在適用自身指導意見的時候無上位法支撐,對于破產審理中的小微企業,界定也是較為模糊的,且不統一。
《企業破產法》第二條對于適用主體作了規定,即可直接適用破產法的情況。破產法第135條規定了可參照適用的主體。同樣,破產審理中,小微企業專門程序也應當明確其對應的適用主體范圍。即什么樣的企業、什么情況下的企業才能適用小微企業破產程序。否則,將小微企業與大中企業再次混為一談,也違背了優化營商環境的初衷。
2.破產受理時,小微企業的特殊狀態
小微企業占據了市場經濟的絕大部分,其發展靈活、創新性高等特點,也伴隨著其抗風險能力較弱。小微企業相較于大中型企業,其經營發展與企業主的專業能力、商業資源或特殊資質為基礎;也面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小微企業在發展中,比大中型企業更容易陷入困境。
和正常經營的企業不同,很多小微企業在進入破產程序前,可能已因陷入困境而縮小經營,甚至已停止經營。其從營收規模和人員數量上已和正常經營時發生了徹底變化。如果按照正常經營企業的標準去衡量,不利于對破產程序中小微企業的界定。而部分中型企業在發展陷入困境后,面臨減產、裁員,其很可能在某項劃型指標上逐漸步入小型企業甚至是微型企業的界定標準中;但如果按工信部標準,則其可能無法進入小微企業專門程序。
(二)破產程序對于小微企業如何界定
參照其他國家經驗以及我國關于小微企業的界定標準,筆者認為可適當延用國家相關部門規定,即按工信部行業劃型標準來界定小微企業;對于破產案件受理節點確已經營異常的小企業,無法按照或難以按照工信部劃型標準判定的,則適用債權人人數、負債總額、資產總額標準擇一的條件予以認定。
1.以工信部的劃型標準為參考,并應作適當調整
2018年《中小企業促進法》實施以來,已有六年多,我國經濟發展已經歷了數個行業的興衰迭代。而中小企業促進法應會同有關部門制度,報國務院批準的劃定指標卻仍未更新,仍廣泛應用2011年工信部版的劃型標準。
重慶破產法庭在破產審判白皮書中也對破產企業區分行業類型情況作了分析:案涉企業所屬行業數量位居前五的為制造業108家、批發和零售業92家、建筑業64家、房地產業43家、租賃和商務服務業35家,分別占比21.38%、18.22%、12.67%、8.51%、6.93%。即在小微企業破產中,其實是有一定行業發展特點的。
筆者認為在對小微企業進行統一界定時,應充分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工信部及中小企業促進辦早應及時調整相應標準,對原有行業據實更新、對新興行業進行納入等,使其體系得以完善。
與此同時,我國各地發展水平不同,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發展及全球一體化上走得更快、更遠,而西部地區會稍顯滯后。但隨著國家戰略部署和區域統籌發展,西部經濟也從自身優勢著手,在“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等重大戰略實施下得以大力發展。但在對小微企業劃型時,還是應著眼于區域差異化發展,實施區間化劃型,以兼顧全國各地均能適用。
2.破產案件受理時,關于小微企業的劃分標準
通過前述對北京、上海、南京、重慶發布的小微企業破產相關指引,法院在審理破產案件時,對于小微企業的認定大多會以債權債務關系明確、財產狀況清楚、債權人人數不多等程度性描述。但實踐中我們會發現,每一個破產案件都有其特殊性,小微企業亦然,有可能是行業特性產生的特殊性,也可能是企業主個人特色產生的特殊性。對于界定標準的描述,在破產法修改時應盡量明確。
鑒于小微企業行業不同、困境不同、價值不同、規模不同等因素,筆者建議在破產案件審理中,對于小微企業可采取國家相關部門規定或特定條件的方式,即在審理的時間節點,小微企業只要滿足其一,即可進入小微企業的專門破產程序。各地指引中均表述較為模糊“債權債務關系明確”“財產狀況清楚”,但實踐中即便是小微企業,管理人在進場后審核也可能發現個別債權債務關系較為復雜、個別財產狀況較為復雜的情況。在破產法修改時,筆者認為應對小微企業的劃分標準確定一個相對明確的范疇,如:債務總額在1億元以內,或債權人數規模在100人以內,即可納入小微企業專門破產程序范疇。
3.破產案件辦理過程中,應有程序轉換的通道
破產法院在案件受理聽證中,法院審查所依據的大多是企業自身財務報表、審計報告等材料。在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前已經經營異常、人員裁撤、經營停止的情況下,資產負債相關數據的真實性、有效性將有待進一步考證。在債權人申請破產案件時,關于債務人的財產、債務資料可能更為有限。例如,在案件受理聽證時,債務人企業賬面記載債權人數超過一百人,但管理人進場后通過各項核查,發現債權人數遠不到一百人,是否可及時向法院申請轉入小微企業快速審理程序?反之亦然。在法院裁定受理破產案件,管理人進場后,如確能證明該企業符合小微企業破產條件的,應有程序轉換的通道。
綜上,小微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小微企業有著較高的靈活性、發展的多樣性、較強的創新性,也大多附帶著經營者的個人“色彩”,這是小微企業自身的特點,無法忽視,也不應忽視。小微企業順應經濟發展而大量產生,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周期變化而部分退出舞臺。小微企業經營者在企業破產陣痛中與企業的繼續捆綁與適度“分離”,也應是市場化的必然要求。
筆者認為:首先,應立法先上。破產法在修改時,應對小微企業構建專門的制度,以解決小微企業快速審理的根本問題,也應尊重事實地適度納入“經營者及其家庭成員附條件豁免”制度。各地法院的指引、辦法經過大量實踐,已經能為破產法修改提供實踐經驗和支撐。制度的建立、健全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市場化經濟的發展。而其中到底何為“小微企業”也是應予高度重視,從法律法規上予以明確界定的。其次,可結合中小企業促進法的主體定位,適當延用工信部行業劃型標準來界定小微企業,但劃型標準應及時更新;對于破產案件受理節點確已經營異常的小微企業,無法按照或難以按照工信部劃型標準判定的,則參考適用債權人人數、負債總額、資產總額標準任意滿足其一即可予以認定。讓小微企業應破盡破,以適用小微企業快速審理為主。后如確在審理中發現不符合小微企業條件及案件辦理要求的,及時轉入普通破產程序。這才能發展出適應社會經濟要求的新質生產力。
注 釋
① See Janis Sarra, Micro, Small and Medium Insolvent Enterprises: Do We Need Statutory Reform in Canada? First the Data... then the Reform, in Janis Sarra and Barbara E. Romaine (eds.),Annual Review of Insolvency Law 2015 (Toronto: Carswell, 2016) (hereafter Sarra, Statutory Reform)
② [加]羅蘭德.戴維斯等著:《中小微企業破產模塊法》,韋子唯譯,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8頁
③ [加]羅蘭德.戴維斯等著:《中小微企業破產模塊法》,韋子唯譯,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9頁
④ 木木弓幺,《2021年版日本中小企業白皮書概覽》,載于微信公眾號“PKU數字經濟實驗室”,2021年5月20日
(作者:張涌 張德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