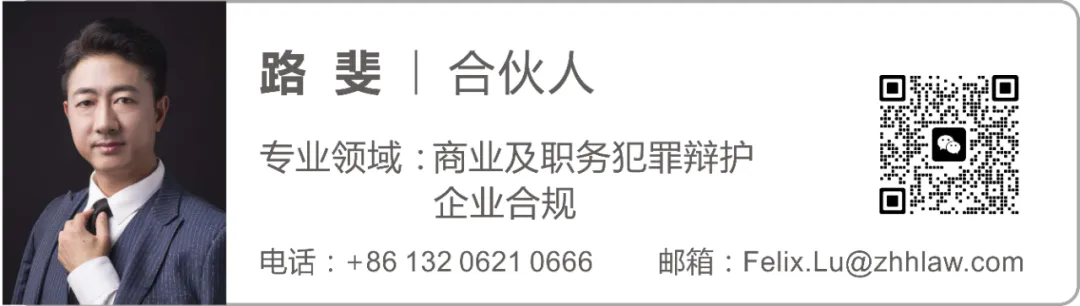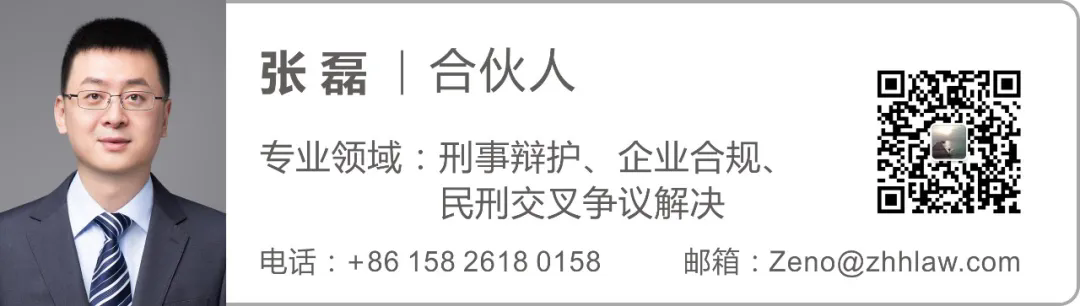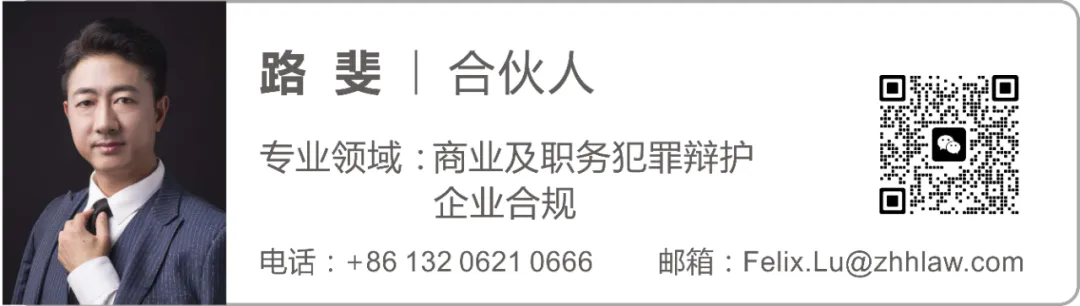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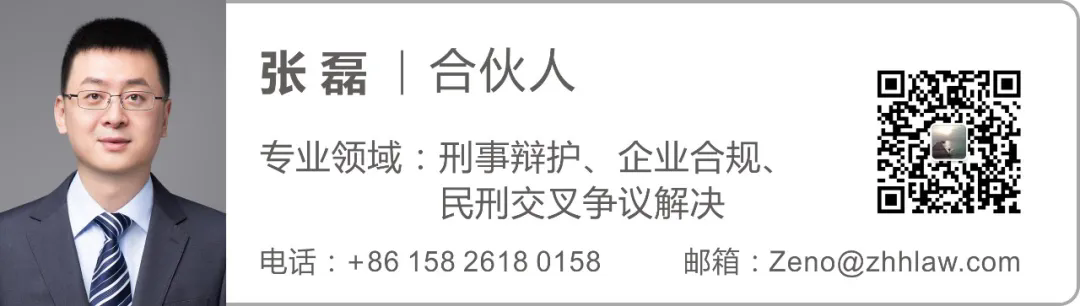
2024年8月19日,“兩高”《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發布,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
洗錢犯罪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經濟金融安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洗錢罪刑法條文作了重大修改,此前最高法于2009年頒布的《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9年解釋》)已略顯滯后。同時,國際反洗錢組織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在對我國反洗錢工作進行評估時,指出了我國反洗錢工作在合規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的問題,迫切需要修改完善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更好地滿足反洗錢工作需要。因此,最高法自2021年啟動《解釋》起草工作,牽頭、會同最高檢,經多輪征求意見和修改完善,制定本《解釋》。
筆者以為,與《2009年解釋》相比,新《解釋》有以下亮點:
亮點一 明確洗錢罪適用上游犯罪種類
《解釋》呼應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于第十二條明確了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為“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七類犯罪。而《2009年解釋》的“大洗錢”思路中所囊括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由于“兩高”正在修訂《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故未規定于新《解釋》。
亮點二 明確“自洗錢”犯罪認定標準
《解釋》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為掩飾、隱瞞本人實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實施該條第一款規定的洗錢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在刑法第191條規定的基礎上,明確突出了為了掩飾、隱瞞“本人”犯罪之洗錢行為,即“自洗錢”行為。
適用中應注意的是:自洗錢行為不同于七類上游犯罪本身,而是掩飾隱瞞該七類犯罪所得及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如為了完成該七類犯罪而以提供賬戶等方式收取款項的行為,應評價為該七類犯罪本身;而后再次進行資金轉移、轉化的行為,無論是提供新賬戶還是使用原賬戶,則有構成洗錢罪的可能。
亮點三 修改“他洗錢”犯罪主觀認知審查認定標準
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刪除了原洗錢罪中“明知”的用語,新《解釋》也不再以“明知”,而是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為“他洗錢”犯罪主觀認知審查認定標準。
《解釋》第三條針對“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認定,采用了“可反駁的事實推定”模式,即司法人員根據行為人行為信息、職業經歷等事實,結合行為人供述和辯解以及證人證言等情況,通過對行為人主觀狀況進行綜合審查判斷、形成“內心確信”。誠然,這種認定模式應該接受“反證排除”之檢驗,因此同條也規定“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解釋》第三條同時也規定了他洗錢的“概括認知”模式,即行為人只要“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罪行包括在七類上游犯罪中,哪怕存在此罪與彼罪的認知錯誤,也不影響司法人員根據客觀事實直接認定其構成“洗錢罪”。
亮點四 豐富規范了洗錢方式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之“其他方法”,在《2009年解釋》規定的基礎上,新《解釋》新增了“通過拍賣、購買金融產品等方式”“通過買賣儲值卡、黃金等貴金屬等方式”,以及“通過‘虛擬資產’交易、金融資產兌換方式,轉移、轉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等幾項行為模式。
《解釋》增加以“‘虛擬資產’交易、金融資產兌換方式”洗錢行為,及時回應了當前虛擬貨幣的活躍度及其在我國的法律定位。虛擬貨幣自誕生以來,已然有發展成為新型交易媒介、躋身主流交易符號的趨勢,但自2021年9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等10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以來,我國當前規范中雖已明確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但對民間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行為的有效性不再給予司法保護。本次《解釋》進一步明確對虛擬貨幣用于非法活動的否定態度,明確規制利用虛擬貨幣掩蓋非法收益或從事不法活動的行為。
亮點五 明確洗錢罪與其他犯罪的競合處罰原則——從重處罰
新《解釋》在《2009年解釋》的基礎上,于第六條進一步明確,構成洗錢罪,同時又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洗錢罪定罪處罰;構成洗錢罪,同時又構成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非法經營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或者幫助恐怖活動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可以認為,《解釋》在處理洗錢罪與其他犯罪的競合時,采取了“從重處罰”的規范思路。
亮點六 明確洗錢罪與上游犯罪事實、罪名的關系
新《解釋》沿襲了《2009年解釋》的規范思路,認為“認定洗錢罪應當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本條規范意義在于,洗錢罪僅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而非以上游犯罪定罪為前提,即上游犯罪之事實,可以作為認定洗錢罪的充分條件,而無論該上游犯罪是否被定罪以及定為何罪。也即洗錢罪的成立不以上游犯罪的判決為前提,仍舊是延續“從嚴”的標準和尺度。
亮點七 明確洗錢罪的罰金數額標準
《刑法修正案(十一)》取消了罰金刑的限額,《解釋》與此相呼應,于第九條規定“犯洗錢罪,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判處一萬元以上罰金;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處二十萬元以上罰金。”可以認為,這種只設最低罰金標準、上不封頂的開放式規范,切實迎合了打擊犯罪之需要,也回應了社會期待,“洗錢者不得因其肉身伏法而躲避高額經濟處罰”。
其 他 《解釋》留白及難點
《解釋》一方面將其他類型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留待其他司法解釋進行詳細規范;另一方面,面對“自洗錢”的各種復雜情形,《解釋》并沒有就“自洗錢”入罪的例外情形以及“自洗錢”犯罪與上游犯罪數罪并罰的問題作出規定,而是留待司法實踐繼續研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司法實踐中,仍然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如對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行為如“自窩藏”行為,不能認為構成洗錢行為;應遵循“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上游罪名通常可能衍生的、與洗錢罪極為相似、或有交叉、或有關聯的犯罪行為,由于牽涉到較為復雜的罪數認定、或犯罪情節評價問題,需要在個案中進行具體判斷,很難一概而論,應慎重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