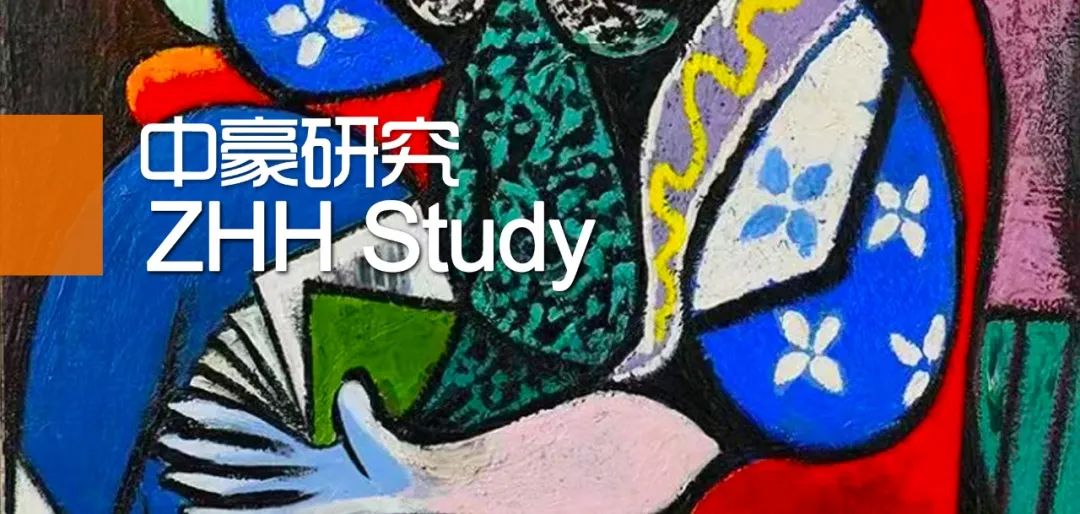
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資法》生效施行,要求外商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需要在五年內調整至與內資企業一致。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修訂通過《公司法》,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對我國公司主體的治理結構作出了新的調整優化規定。對于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資企業而言,需要在依據《外商投資法》進行組織架構調整的情況下,進一步對標《公司法》規定,對治理結構提檔升級。修訂后《公司法》的生效日期,與《外商投資法》規定的五年之期,恰好形成一個短暫的窗口期,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治理結構合規轉型提出了新的挑戰。
窗口期183天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外商投資法》頒布施行以前,我國外商投資企業主要按原《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的規定組織和治理,與內資企業依據《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法規組織和治理的情況不同。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資法》施行以后,根據該法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的要求,外商投資企業須在五年內(即2025年1月1日之前)變更原有結構,新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應當適用《公司法》等法律的規定。而隨著此次《公司法》的修訂,公司形式的外商企業不但要按《外商投資法》的規定按時完成從原三資企業法架構到《公司法》架構的轉型,還需要在修訂后的《公司法》生效后,按修訂后的《公司法》的要求,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提檔升級。
雖然2024年剛剛開始,到《外商投資法》要求的轉型截止日期2024年12月31日尚有一年時間,但對于尚未完成轉型的外商投資企業而言,考慮到修訂后的《公司法》是在2024年7月1日生效,少有企業會選擇在2024年上半年按修訂前的《公司法》先變更一次組織結構,再在下半年按修訂后的《公司法》升級一次治理結構,而一般會選擇在2024年7月1日后一次性調整治理結構到位,以同時滿足《外商投資法》和《公司法》的要求。因此,對于這部分外商投資企業而言,實際上依法調整治理結構的窗口期僅有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這六個月(實際為183天)的時間。
修訂后的《公司法》對公司治理結構設立了新的原則
對以授權管理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次《公司法》修訂,在治理機制、治理結構方面優化力度很大,進一步規范了公司的組織和行為,強化了各方主體責任,有許多制度創新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舉措,也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組織結構轉型升級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外商投資企業股東多在境外,難以直接管理境內企業,因而非常依賴于董事會和管理層進行授權管理的特點。在治理結構方面,《公司法》修訂后的如下調整需要特別注意:
(一)股東會、董事會的法定職權范圍有重大變化,各自職權劃分更加依賴于具體授權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原《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了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的法定職權,對于法定職權外的其他公司權力則統一授權公司章程規定。原《公司法》規定的法定職權,除專屬于股東行使的選任解聘董事和監事、調整公司資本、變更公司章程和形式,以及理應由董事行使的向上對股東會負責和匯報、制定公司運營方案、制定內部制度和向下負責經理有關事項外,還對涉及公司經營的核心內容“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案”在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進行了劃分,將這兩項公司經營的核心事項交由董事會制定、股東會行使,涇渭分明。修訂后的《公司法》將“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審議批準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從股東會的法定職權當中刪除,將“制定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從董事會的法定職權當中刪除,而將這幾項重要職權的劃分也交予了公司章程的規定,實際對與公司經營相關的核心權力在股東會、董事會之間的劃分交到了公司章程手中,由全體股東在章程制定過程中預先共同決定。
此外,原《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對于股東會、董事會法定職權可否限縮、可否授權的問題沒有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較大爭議。而修訂后的《公司法》明文規定可以授權董事會決議發行公司債券外,原則上并不允許股東會將法定職權授權董事會行使。而根據修訂后的《公司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原則上公司章程可以限制董事會法定職權,公司對內可以將董事會的法定職權進行限縮或收歸股東會行使。股東會收束董事會權力后,可以再視情況將有關職權授予董事會行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為了保護與公司交易的善意相對人的利益,修訂后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對董事會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限縮董事會的法定職權對內有效,而對外則僅具有受限的對抗力,容易發生效力爭議。
這些規定導致公司章程關于股東會、董事會權力的劃分的規定較以往更為重要。如有不慎,一方面很有可能導致受委托進行代理管理的董事會權力過大,從而擠占股東對與公司經營相關的重大事務(如核心的決定公司經營方針、投資計劃,以及批準公司年度預算和決算等)的決策權、管理權;而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章程限縮董事會權力,重大事務皆由股東會行使和決策,不僅影響管理效率,而且對外又不具有對抗效力,極易引起糾紛。同時,由于修訂后的《公司法》對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行權進行了明確規定,授權的議事規則、具體機制將對公司股東話語權的博弈產生巨大影響,需要審慎決定。
由于本身的特點,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東直接參與公司經營困難相對較大,且各方股東可能存在不同意見,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要求各股東在2024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窗口期內,對各自參與企業治理的權力劃分進行詳細探討、達成一致、明確規定,同時做好對董事會職權的規劃、管理工作,無疑對各股東方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二)經理的職權不再由法律規定,管理層完全依據公司章程規定和董事會授權進行具體管理
除對股東會、董事會法定職權進行調整外,調整后的《公司法》直接刪除了經理的法定職權,規定經理職權完全由公司章程和董事會授權決定。在此情況下,外商投資企業不僅要考慮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職權劃分,還要對經理的職權有清晰的計劃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東方可以在章程中明確經理職權,但基于公司章程的穩定性和經理工作靈活性的沖突,大部分經理職權仍應考慮由董事會根據具體情況向下授權。這樣,在公司章程制定過程中,各股東就需要做好全盤的規劃和考慮,不僅需考量董事會權力的分配,還需預先考慮更為具體的經理職權問題,畢竟較大比重的經理職權將可能依賴于董事會的直接授權。
(三)董事、高管被賦予了新的職責和定位,履職要求進一步嚴格,職務責任加重
對于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的外方股東而言,自行委任或委派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參與公司管理,選任己方人員擔任高管負責公司運營是普遍的操作方式。而對于董事、高管,修訂后的《公司法》提出了更高的履職要求,履職責任更加嚴格。如根據修訂后的《公司法》的規定,公司董事會負有對股東出資情況的核查、催繳義務,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有關董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出現股東抽逃出資的,負有責任的董事、高管還應與股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公司的監事會可以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交執行職務報告,對不盡職董事、高管可以提出解職建議等。外方股東在自行或委派己方人員擔任相應職務時,應當將這一因素納入考量,充分考慮自身是否具備全面、勤勉履職的條件(如語言因素、地理距離因素、時差因素、對國內情況的了解程度等),不能董而不事,高而不管。在此情況下,不再建議由外方股東自行擔任或隨意選擇利益代表人擔任公司的董事、高管職務,公司董事、高管的選任問題,將成為外商投資企業股東需要慎重考慮的新問題。
(四)引入單層治理結構,審計委員會可以代替監事會行使監督職責
允許公司不設監事會,而在董事會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職務是本次《公司法》修訂的重要亮點之一。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來說,這一新機制的引入,勢必導致股東各方對于董事會席位安排、審計委員會席位安排的爭奪更為激烈。除了在公司章程明確有關審計委員會的相應規定外,為了確保審計委員會本身的有效運行、避免新機制淪為擺設,各方股東還需要對審計委員會成員選聘要求和程序(一定程度上影響股東各方監督權力的分配)、議事規則等進行詳細探討、約定,和章程一起作出統一規劃。對于如何安排合理人員,如何完善審計委員會的議事機制、決議規則,都是外商投資企業及各方股東需要面對的新挑戰。
關于應對窗口期
合規優化調整公司治理結構的建議
由于本次《公司法》的修訂,外商投資企業按照《外商投資法》的要求對組織形式、組織機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升級治理結構的窗口期實質性縮短,需要完成的工作量級式增加。而外商投資企業又往往面臨股東分散在國外、溝通存在時差和語言問題,對國內法律及政策環境的理解較少,各股東基于各自國別對法律認識存在思維慣性,股東簽署文件不便、會面不便等困難,進一步加大了工作難度。加之各股東方本身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對于在合資企業的話語權、監督權、人員安排有不同的考慮,對治理結構的調整還存在無法快速達成合意、存在博弈商討過程的問題。
在此情況下,我們建議外商投資企業提前布局,在修訂后的《公司法》生效前提前謀劃,通過聘請專業律師等方式對修訂后的《公司法》新的要求、新的機制進行充分了解,加強股東間的預先溝通和商討。可能因本次調整導致新一輪股東間博弈的,可以考慮由律師團隊提前介入,爭取有利于己方的談判條件。對于地域、時間、語言方面的差異和困難,一方面可以通過時間換空間,早做打算;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專業力量,拉平各方在語言、背景知識、法律認知方面的差別,提高談判效率。在前期準備充分、各方提前達成初步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在2024年7月1日修訂后的《公司法》生效后,公司可以集中精力于推進文件草擬、簽署、落實等工作,如期依法完成治理結構的調整要求。
(作者:范珈銘 徐姣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