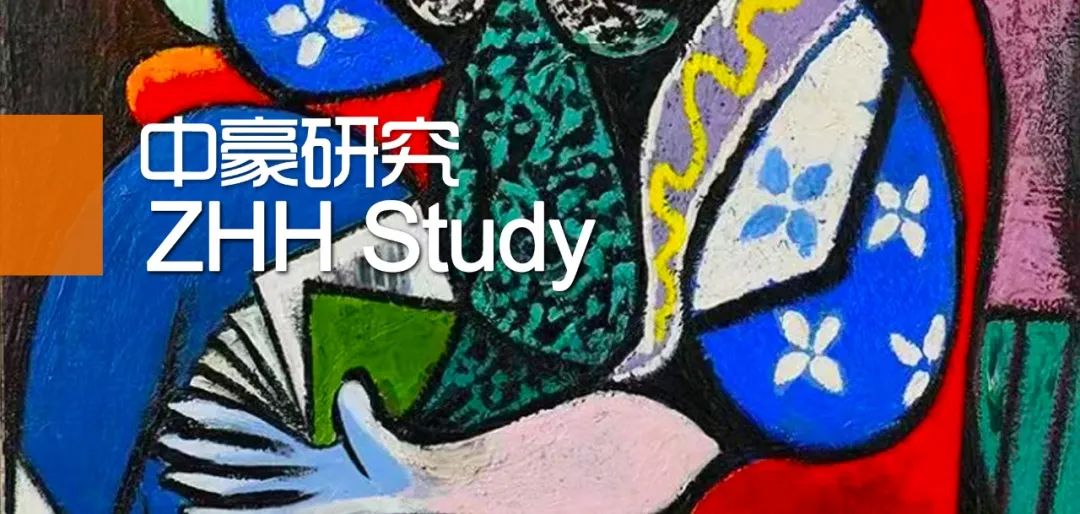
摘要:破產清算案件中,管理人處理債權基于以物抵債協議提出的各種請求時,首先應當研判基礎債權協議是否存在可被撤銷、被宣告無效或被認定不成立等情形,然后從以物抵債協議本身的效力以及抵債財產的法律狀態這兩個層面,研判以物抵債本身是否有效。在此過程中,管理人還應當依據破產法理論及規定,研判是否應當主動行使撤銷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以物抵債協議。
關鍵詞:破產清算 以物抵債 協議效力 撤銷權
基礎債權協議的效力研判
以物抵債是為實現目標債權而設,基礎債權協議就是以物抵債的“地基”,如若基礎債權協議本身未能依法有效設立、可被撤銷或者應屬無效,那么以物抵債可能自始欠缺生效條件,此時,管理人需考量基于何種具體合法事由或采取什么舉措,以拒絕債權人的以物抵債請求。
拙見以為,通常情況下,基礎債權協議可被撤銷的,管理人原則上應起訴撤銷基礎債權協議;基礎債權協議未有效設立、自始無效或者被撤銷的,管理人理應通知解除以物抵債協議;管理人拒絕債權人的以物抵債請求后,理當提示債權人可以基于協議被撤銷或被解除,就其損失依法申報金錢債權。
原因在于,第一,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以下簡稱《破產法解釋二》)第九條第二款的規定,管理人負有主動行使撤銷權,以避免債務人財產不當減損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管理人不僅需要關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的可撤銷情形,還需關注基礎債權協議是否存在重大誤解、欺詐、脅迫、顯失公平等可撤銷的情形。但尷尬之處在于,管理人往往很難通過外部調查手段獲悉協議是否存在重大誤解等可撤銷情形。因此,為免履職疏漏,建議管理人向債務人發函詢證并留痕,詢問債務人協議有無重大誤解等可撤銷的情形。
第二,債務人和債權人設置以物抵債的合同目的是代物清償目標債權,如若基礎債權協議本身未成立、被撤銷或者被宣告無效的,那么債權人實際并不享有抵債的目標債權,債權人實際享有的是依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五百條等規定產生的賠償請求權。鑒于此,債務人不應當繼續履行以物抵債的相關義務,管理人自然不應當認可債權人的以物抵債請求,但可以引導債權人依照前述規定申報金錢債權。
在各種以物抵債中,管理人需要重點關注、審慎處理基于工程款債權設立的以房抵款情形。原因在于:首先,建設工程領域存在較多效力性的強制性法律、行政法規,且建工市場實踐中,轉包、違法分包、掛靠、招投標違法等等情況屢見不鮮,施工合同無效的情形紛繁復雜,加之以房抵債是建工領域清理工程欠款的常用方式。因此,管理人在處理涉及建工領域的以物抵債相關請求時,更容易遇到以房抵款的基礎債權協議(施工合同)無效的情況。再加之,工程款債權的數額往往較大、涉及面廣,僅此一點,就值得管理人對建工領域的以房抵債問題傾注更多的注意力。
其次,按照《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條的規定,施工合同無效但工程質量經驗收合格的,承包人依然有權參照施工合同關于工程價款的約定取得工程價款。嚴格來講,債權人依據前述規定享有的“折價補償”的法定請求權有別于基于施工合同享有的合同請求權,但債務人與債權人簽訂以房抵債協議時,普遍不會刻意甄別施工合同是否有效,雙方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在明知施工合同無效情況下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因而,即便施工合同無效,債權人也依法享有取得工程價款的債權,管理人很難簡單地以基礎債權協議無效、工程款債權無效、亦或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一致等事由,一刀切地拒絕工程價款的以房抵債請求。
最后,拙見以為,即便施工合同無效,基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以下簡稱建工優先權),施工人在特定情況下享有繼續履行以房抵債協議的權利。根據《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即便施工合同無效,債權人依然可能對工程價款享有優先受償權,這就為其提出的繼續執行以房抵債提供了可能性。
綜上,管理人拿到債權人基于以物抵債協議提出的各類請求后,建議首先要求債權人提交基礎債權協議,先行研判基礎債權協議是否有效,以便判斷債權人提出以物抵債相關請求的基礎是否成立、有效。遇到基于工程價款債權提出的以房抵債請求時,可以參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于印發建筑工程施工發包與承包違法行為認定查處管理辦法的通知》等文件規定的違法情形,細致研判施工合同的效力。
民法理論視角下
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研判
我國《民法典》并未明文規定以物抵債的構成要件,參考論述以物抵債的繁多著述,以物抵債的效力大致取決于兩個層面的法律事實和狀態:一是以物抵債協議本身的效力,二是抵債財產的法律狀態。
(一)物抵債協議的效力研判問題
該問題主要考察締約主體是否適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實,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是否違背公序良俗。除此之外,管理人需要特別關注以物抵債協議簽訂時,債務履行期限是否已經屆滿的問題,這可能是管理人研判以物抵債效力的疑難點之一,因而以下稍作展開:
第一,參考《九民紀要》第44條的規定,關于履行期限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如無其它無效事由,也不存在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等情形的,該類協議通常不存在無效之虞。
第二,對于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九民紀要》第45條并未對其效力明示法律意見。但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做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6153號民事裁定書中,對于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商品房抵工程款協議書》,最高法明確支持了原判決認定該協議無效的裁判結論。此外,從體系解釋與反對解釋的角度來看,如果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有效,那么人民法院應當按照《九民紀要》第44條處理,即考慮支持債權人交付抵債財產的請求,由此可見,《九民紀要》特別規定第45條,要求法院釋明、請債權人按照原債權債務關系起訴,其立論基礎就是不認可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有效。
第三,關于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另有部分著述進一步認為 ① ,應當區分締約方是否明確約定放棄期限利益,如果已經明確放棄期限利益的,可按照履行期限屆滿后的以物抵債規則處理;如果沒有明確放棄期限利益的,則參照讓與擔保處理。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亦認可將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按照擔保處理。②
第四,另從司法案例來看,以物抵債協議是否簽訂于履行期限屆滿前并非是百分百硬性的效力評判標準。這一點可以參見最高法民申7497號民事裁定書,在該案中,最高法表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基礎法律關系是以物抵債協議,該《商品房買賣合同》雖然形成于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幾日,但在債務履行期滿后債務人明確了買賣合同的房屋具體信息、單價等,并確認付清房款,應當認定雙方系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
綜合上述觀點、意見,管理人或許可以參考以下要點審查、處理以物抵債協議的簽訂時間與其效力之間的關系問題:
首先,存在下述任一情形,并且,協議不存在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及其它無效情形的,管理人可以在認可物抵債協議有效的基礎上,進一步研判能否支持債權人的以物抵債請求:
① 以物抵債協議簽訂于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的;
② 以物抵債協議雖然簽訂于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但債務人明示放棄期限利益的(如確認債務加速到期等情形);
③ 以物抵債協議雖然簽訂于期限屆滿前,但債務人在期限屆滿后(原則上破產受理前)再次確認以物抵債意思的(如協定抵債財產的位置、數量、價值等)。
其次,除前述情形外,如果以物抵債協議簽訂于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的,或者管理人經審查認為以物抵債協議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管理人原則上應當向債權人釋明,并勸導債權人依據原債權債務關系,向管理人申報金錢債權,而后在金錢債權的審查確認過程中,再行研判該債權人申報的金錢債權是否應當優先清償。
最后,債權人(包括以物抵債的債權人和其他債權人)對管理人作出的上述認定意見有異議的,應當及時告知債權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原因在于,管理人并非司法機關,管理人自行對以物抵債協議作出的效力評判,該行為實質上等同于債務人自己承認或拒絕債權人的行權主張,不具有終局的既判法律效力。為保障債權人及時行權,也為盡早確認債務人財產的法律狀態,管理人有必要提示債權人盡早起訴確權。
(二)抵債財產法律狀態的研判問題
關于抵債財產的法律狀態,部分文章總結的關鍵考量因素包括債務人或第三人對抵債財產是否享有處分權 ③ 、抵債財產是否合法且可流通 ④ 。其論證理據多為參考《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三百九十九條關于抵押權有效設立的規定。
拙見以為,雖然以物抵債本質上是一種債務清償方式的特別安排,與抵押權存在本質差別,這些文章直接將抵押權的構成要件套用到以物抵債,其論證路徑可能有待商榷,并且以物抵債協議是否有效與以物抵債能否履行應當是兩個層面的法律問題。但好在對于管理人而言,如若債務人對抵債財產沒有處分權,或者抵債財產不可流通,那么管理人對其的處理結果與以物抵債協議無效應是一致的,即不予認可債權人提出的取回權或者繼續履行主張,管理人可以告知債權人申報衍生的金錢債權;債權人如有異議的,可以告知其及時向人民法院起訴。
此外,關于債務人對抵債財產是否享有處分權的問題,管理人可以關注以下兩點問題:
第一,前文提及的“處分權”不僅僅是指債務人對抵債財產享有轉讓的權利,更重要的判斷標準是債務人是否有權最終享有處分抵債財產所得的收益。原因在于,一方面,債務人有可能基于委托、代售等合同關系享有處分抵債財產的合同權利,但并不一定享有抵債財產的所有權;另一方面,按照《破產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即便已經貨交承運人,在法定情形下,出賣人依然享有取回權;再一方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商品房消費者權利保護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商品房消費者批復》)的規定,在享有“超級優先權”的商品房消費者放棄房屋交付請求權之前,管理人經行處分債務人名下登記的商品房可能侵害商品房消費者的權利,并可能進一步引發群體性事件。
可見,管理人評判“處分權”時,不能僅僅看形式上的權屬登記狀態或者占有狀態,畢竟第三人有可能向管理人行使取回權或者其它優先請求權。值此情況下,債務人名義上有權處分抵債財產,這并不一定意味著處分抵債財產所得收益就歸屬于債務人,管理人自然不應當將抵債財產用于繼續履行以物抵債。
第二,判斷“處分權”狀態的時間點應當是債權人提出以物抵債請求的時點。理由與上一點相似,破產受理后,由于破產法規則以及管理人行為的介入,債務人財產可能因為取回權、撤銷權、解除權等法律原因發生根本變化,債務人對抵債財產可能喪失處分權,也可能取得處分權。因此,如若僅僅站在以物抵債設立或者破產受理等時點,孤立、靜止地研判抵債財產的法律狀態,那么所得結論有可能脫離實際情況,致使管理人的處理結果損害債務人、債權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或者引發更多的權屬糾紛。
破產法視角下
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研判
拙見以為,在確認以物抵債及其協議有效之后,管理人還有必要參照《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研判是否應當主動行使撤銷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以物抵債協議。
(一)主動行使撤銷權的必要性問題
第一,從管理人職責角度看,“多走一步”利于保護管理人自身。如前所述,《破產法解釋二》)第九條第二款是債權人督促管理人積極行使撤銷權的“緊箍咒”,為免部分債權人將債權無法足額清償的“火”燒到管理人身上,管理人有必要審慎履職,進一步研判是否應當主動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
第二,管理人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更可能利于實現破產法的立法目的。破產清算程序中,公平清償是基本原則,如若以物抵債協議涉嫌存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情形的,管理人有必要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盡可能實現債權人之間的公平清償結果;而在破產重整與破產和解程序中,如若能夠依法避免個別清償、提前清償,這就變相達到了避免債務人財產縮減的效果,進而更有可能促成拯救債務人的良性結果。
第三,管理人對“以物抵債協議是否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法律評判(以下簡稱惡意侵權評判)無法替代管理人撤銷權的行權評判。惡意侵權評判與管理人撤銷權評判均意在維護第三方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由此可能推導出這樣一種結論:如果已經得出以物抵債協議沒有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這一結論,那么就沒有必要再討論是否對以物抵債協議行使撤銷權了。
其實不然,惡意侵權無效制度與管理人撤銷權制度是兩套不同的法律制度,無法簡單地以惡意侵權評判替代管理人撤銷權評判。具體而言:首先,二者對債務人主觀過錯的評判標準不同。民法理論中“惡意”具體包括“明知”和“明知且具有損害他人的意圖”兩種 ⑤ ,而《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并不以當事人存在主觀過錯作為適用條件。其次,所保護法益不同。惡意侵權具有明顯的不法性,法律應當給予否定性評價,以維護第三人合法權益以及市場經濟秩序、公序良俗,而管理人撤銷權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是恢復債務人的財產,使全體破產債權能夠公平受償 ⑥ ,以實現全體債權人利益的實質公平。然后,限制條件不同。惡意侵權評判無需考究惡意侵權行為與破產受理時間點之間的關系,管理人撤銷權則受制于破產受理前一年內以及六個月內的法定情形。最后,邏輯順序不同。通常而言,撤銷的對象應當是已經生效的法律行為,換言之,管理人撤銷權評判應當置于惡意侵權評判之后。
故,管理人撤銷權能夠實現《破產法》特有的公平清償等立法目標,彰顯破產程序中管理人的獨特價值,這是惡意侵權法律評判力所不及的。因此,即便已經認定以物抵債協議不存在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情形,管理人也有必要單獨研究評判是否應當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
(二)主動行使撤銷權的可行性問題
所謂可行性,主要是指管理人能否準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的問題。拙見以為,對于破產申請受理前一年內設立的以物抵債協議,其中抵債財產的折價數額明顯不合理的,管理人可以援引《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的”,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對于破產申請受理前六個月內設立的以物抵債協議,如果債務人簽訂以物抵債協議時已經具備破產原因的,管理人應當援引《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請求撤銷以物抵債協議,但以物抵債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
由于以物抵債本身就是個別債務清償行為,管理人按照《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處理自不待言,以下僅就管理人適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處理以物抵債協議展開論證。
1.將管理人撤銷權應用于以物抵債,第一個法律難點在于以物抵債是否屬于《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的“交易”行為。拙見以為,以物抵債理應基于對抵債財產折價的磋商過程,因而交易是該行為的底色 ⑦ 。
具體而言,首先,以物抵債明面上是以抵債財產的所有權清償債務,債權人直接取得抵債財產的所有權,形式上與流押異曲同工。我國法律對于流押條款的法律評判基調依然是無效,但參考《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條的規定,如果債務人與債權人就財產達成了折價協議,那么雙方之間的折價行為應屬歸屬型清算 ⑧ ,債務人將財產按照折價數額抵償債務的清償行為有效。參考前述有關流押的規定及法律意見,債務人與債權人理應對抵債財產有一個價值商定或價值折算的磋商行為,唯此清算過程,以物抵債才能夠按照當事人的意思發生法律效力。否則,所謂的以物抵債極大可能淪為流押條款規避法律限制的軀殼,可能對債務人不公,也可能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
其次,從實踐來看,以物抵債協議通常會列明雙方商定的抵債財產的價值,并以該價值數額等額清償債務,這表明抵債雙方通常存在將抵債財產定價折算的磋商過程。
最后,基于財產價值折價磋商過程的代物清償,本質上是交易行為的交付簡化。債權人按照商定的價值數額取得抵債財產所有權,本質上仍是等價交換,中間省略了債權人向債務人支付價款以及債務人以價款向債權人清償債務的兩次交付行為。較為直觀體現其交易屬性的表征就是雙方為以物抵債簽訂的買賣協議。
故,從雙方商定抵債財產價值以及等價交換的本質來看,以物抵債行為的底色仍是交易,應當能夠適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予以規制。
2.如何評判“明顯不合理的價格”是適用《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的另一個技術難題。拙見以為,原則上應當依據以物抵債協議簽訂時、抵債財產所在地的市場價格作為評判基準,輔以70%的標準線,綜合其它適當因素判斷抵債財產的折價數額是否明顯不合理。
首先,關于財產價值判斷的時空基準,原則上應當是以物抵債協議簽訂的時點,空間基準原則上應當是抵債財產所在地。司法實踐中,部分管理人證明價格明顯不合理的依據是協議簽訂后某個時間點生成的數據,如(2019)鄂民申1836號案件中,證明價格不合理的材料為評估報告,而評估基準日是抵債協議簽訂后一年多的某個日期。
雖然《破產法》尚未詳細規定評判財產價值的時空基準,但我國債權人撤銷權制度已有相對成熟的類似規定。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已失效,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二》)第十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參考交易當時、交易地的物價部門指導價或者市場交易價。當然,債權人撤銷權制度與管理人撤銷權制度略有不同,債權人撤銷權制度要求以交易當時、交易地作為時空基準,其目的在于判斷債務人與受讓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意,“只有以實施交易行為時作為判斷基準才能彰顯其惡意” ⑨ 。而《破產法》設立管理人撤銷權的立法目的在于維護公平清償原則,債務人的惡意并不是行使管理人撤銷權的必備要件,因此,債權人撤銷權的時空基準規定僅可作為適用管理人撤銷權的參考。
回到《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原文,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涉及債務人財產的下列行為”,具體包括“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從文義上看,管理人撤銷權的對象是債務人的交易行為,理應回溯到債務人交易發生時的行為狀態,評判其交易價格是否明顯不合理。前述條文并沒有規定以管理人接管后的財產價值狀態評判債務人事前交易行為的合理性,否則,管理人撤銷權可能嚴重沖擊市場交易的安全性與穩定性。
綜上,按照《破產法》條文文義,并參考債權人撤銷權相關規則,管理人理應以物抵債協議簽訂時、抵債財產所在地的市場價格作為判斷抵債財產的折價數額是否明顯不合理的依據。
其次,參考債權人撤銷權相對成熟的制度經驗,管理人可以將70%作為評判明顯不合理的標準線。參考《合同法解釋二》第十九條的規定,轉讓價格達不到市場價格70%的,可視為明顯不合理的低價。如若抵債財產的折價數額不足協議簽訂時財產市場價的70%的,管理人可以考慮將該以物抵債協議納入撤銷對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適用債權人撤銷權制度過程中,70%的標準線也不是硬性指標,還需要考慮抵債財產的權利期限、質保期限、權利負擔等等特殊情況對財產價值的影響。
最后,個別案件中,人民法院還考量了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聯關系、交易動機和目的、支付能力狀況以及交易程序等影響因素,具體參見(2022)魯04民終709號二審民事判決書。
故,對于破產受理前一年內以及半年內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管理人有必要按照《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審查研究是否應當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綜上所述,以物抵債有效設立是債權人提出的取回權請求、繼續履行請求的前提和基礎。圍繞以物抵債效力這一難點,管理人應當從基礎債權協議效力、以物抵債(包括以物抵債協議)效力以及管理人撤銷權等層面,層層剖析。唯有在以物抵債有效的前提下,管理人才有必要進一步研判能否行使單方解除權、債權人能否行使取回權、以物抵債能否繼續履行等等問題。
(作者:寧思燕)
注 釋
① 楊婧:《司法實踐中“以物抵債”的八大疑難問題|審判研究》,2023年3月14日發表于“審判研究”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2wshu6nvDaixXuw_vg_MXA。
② 賀小榮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會議紀要(第三輯)》,2022年7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8頁。
③ 王彬:《兩萬字實操手冊:以物抵債全方位解讀》,2023年6月6日發表于“淄博市破產管理人協會”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MKcUjuTHyD_fB4sf91rayQ。
④ 楊元元 吳志斌:《以物抵債專題(四)| 以物抵債協議的生效要件與效力認定規則》,2023年6月14日發表于“永嘉信律師事務所”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IoS0zfDiTvBsZJ8WkRYjFw。
⑤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理解與適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第776頁。
⑥ 龍泳宏:“破產程序中撤銷權制度研究(上)”,2023年1月9日發表于“中豪法苑”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zSvco9-odxfdX6GhpSD8RQ。
⑦ 注:關于以物抵債是否屬于交易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認為并非所有的以物抵債都具有“準買賣合同”的性質,不具有“準買賣合同”性質的以物抵債包括:司法程序中的以物抵債,履行期限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履行期限屆滿后達成且已經取得抵債財產所有權的以物抵債,具體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會議紀要(第三輯)》(賀小榮主編),2022年7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8頁。
⑧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理解與適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071頁。
⑨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理解與適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第536頁。

